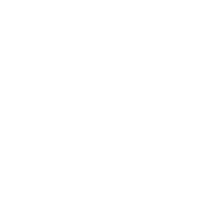0755-23282306136 4236 3915

4月25日,中兴通讯发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,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93亿元,同比增长6.43%;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1亿元,同比增长1.60%。一向低调安静的中兴,因其千亿级别的营收迅速引起关注。
说到我国通讯科技企业,华为无疑是最受瞩目的,从推出鸿蒙系统,再到欧拉系统,一路高歌,其一举一动都能吸引无数人关注。相比之下,中兴通讯显得安静许多。
中兴通讯从成立至今,已走过了37年,是全球头部通信设备制造和解决方案提供商。在国内、欧美等地设立研发机构,业务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,服务全球1/4以上人口,如今是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提供商,全球市场占有率10%。而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,中兴集团创始人,现年81岁的侯为贵老先生。
30年间,侯为贵以敢拼无畏的精神和数次英明决策,带领中兴打败了西门子、诺基亚,集诸多荣誉于一身。
1
初创中兴,披荆斩棘
中兴于1985年由侯为贵一手创办。
那时的中国,正被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建设大潮袭卷。通信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产业,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,邓小平曾指示:“中国发展经济、搞现代化,要从交通、通信入手,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”。
进入80年代,在钱学森的主张下,侯为贵所在的中专学校被改为航天部691厂,从事半导体技术研究。
期间,作为毕业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技术骨干,侯为贵被派往美国学习。在那里,他不仅学到了技术,更对市场、成本等商业知识产生了兴趣,比如做集成电路的电镀时,并不需要国内做的那么厚,“那是乱撒钱”。
回国后,不甘心当一辈子技术员的侯为贵决定创业。1985年,40岁出头的他说服领导,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。
最初侯为贵想做IC(集成电路),但烧不起钱,为了生存,他从电风扇、电话机等做起。通过做电话机,侯为贵接触到了数字程控交换机。
当时数字程控交换机在国内刚刚兴起,中国市场被NEC、爱立信、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,分别有来自7个国家、8种制式的机型,业界流传着“七国八制”的说法。
侯为贵意识到大势已至,本土厂商的机会就在眼前。
“一无图纸、二无资料、三无设备、四无专业人员”的侯为贵力排众议,走上自主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之路。
经过两年努力,1989年,第一台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在中兴诞生,因产品重点针对农村市场,中兴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。
凭借这款产品,中兴摆脱了苦日子,销售额很快突破一个亿。
但苦恼随之而来,股东们开始为利益而争,侯为贵适时做出股权改革——管理层团队自筹资金,成立维先通,与两家国有股东691厂、深圳广宇,共同组建中兴通讯。
这一制度设计,在国内开创了“国有控股,授权经营”的全新模式,使中兴避免了国企“巨龙”式的悲剧,更为中兴争取到更多的自由空间。
伴随着产品向传输、接入、视讯、电源、移动、光通信等多元化领域扩展,中兴步入快速发展阶段。业绩屡创新高,2000年销售额破百亿,2004于香港上市,成为内地第一家A+H上市公司。
2014年,中兴成为紧居华为、爱立信、阿尔卡特朗讯之后的全球前四大通信设备公司。
2
与任正非的相爱相杀
“华为是狼,中兴为牛”。狼吃肉,牛吃草,双方貌似应该互不冲突。但自从1996年首次正面交锋以来,却是狼牙对牛角、针尖对麦芒,激烈混战整整20年。从国内到国外,双方相爱相杀的剧情一波三折,令人惊叹。
从惺惺相惜,到相爱相杀20年
两人的“恩怨”从任正非赴深圳创业的那一天就开始了。起初,两人惺惺相惜,一起探讨民族通信业的未来,之后竞争日趋激烈,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到最后的刀刃相见。
激战始于1998年。那一年,华为在湖南、河南项目的投标书中,加入了打击中兴的内容。第二天,中兴开始反击,如法炮制。结果,中兴赢得了订单。
任正非不甘示弱,随后在法院起诉中兴,指责对方作引人误解的对比。很快,侯为贵便以相同的理由状告华为。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。
以侯为贵的性格,他不太愿意大动干戈。据说,华为刚开始告中兴时,他一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起诉。后来,随着竞争不断加剧,他也就慢慢习惯了。
在这场“中华”大战中,中兴赢得了更多赔偿,而华为则赢得了更多市场。
此后,双方的“战火”延伸至国外,在印度、尼泊尔等地展开激烈争夺。这期间,双方你争我斗,半路截住对方投标人员的事情时有发生。
“拼杀”的结局大家都已知道,以华为甩中兴几条街而告终。2015年10月中兴通讯发布第三季度财报显示,中兴通讯实现营业收入685.23亿元,同比增长16.53%;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26.04亿元,同比增长42.19%。而华为2015年的业绩是3900亿元。
作为成立于同时代,分别起步于体制内外的两家高科技企业,中兴、华为成长环境迥然相异,两家企业被植入天冠地屦的企业文化基因,核心竞争力早已霄壤之别。
秀才遇上兵
两家创办时同领域的公司,却逐渐发展为文化氛围迥异的两家企业。其中,掌舵人的性格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任正非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,当过红卫兵,因父母在“文革”期间的不幸遭遇,个人成长道路上承受了较大的政治压力,因此一贯追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。他毕业于重庆邮电学院,内心深处崇拜技术和技术英雄,毕业后进了企业,却成了非主流,养了几年猪。他当过兵,当过“十二大”代表,军旅生涯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,一些人因此称他为“一介武夫”。部队转业后南下深圳,曾流落街头,1988年集资创办民营企业华为公司。经历可谓“大起大落”。也有不少业界人士评价他为“偏执狂”。
比起任正非,侯为贵的经历显得很“平坦”:上学时是尖子生,毕业后教了两年书,后来进入691厂,从技术工人到车间主任,再到技术科长,始终是厂里技术水平最高的专家,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。他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。1985年南下深圳,借款创办国有企业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。
这样的背景使两个人的经营管理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:侯为贵稳健,很少有过激行为,可谓又红又专;而任正非则狼性十足,严厉而富有攻击性,在经营上也敢于冒险,不循常规。据说当年华为与中兴的系列官司爆发后,侯为贵很长时间想不通:华为为什么要起诉中兴呢?不少人就说侯为贵是“温和的机会主义者”。
技术暖男VS铁血军人
作为工程师,侯为贵比较强调沟通,为人宽容,强调经验;而作为军人的任正非则更强调服从,强调对人的主观控制和统一性。
侯为贵处事谨慎而谦虚、勤俭、身体力行、知人善任、正直、重情、善于倾听、好学不倦,相信物质与精神同等重要,强调中庸和平衡;而任正非爱憎分明、强势、我行我素、严格而寡情、果断、强调结果导向、强调纪律、规范,相信物质对人的激励作用,在做思想工作时强调灌输而非双向沟通。
这些性格反映到经营管理中就是:侯为贵善于授权,每个事业部经理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,中兴近20个高级经理在过去一、二十年中都保持了相对稳定。尽管侯为贵的权威地位不容置疑,但具体的管理主要依靠5个层次的经理人。侯为贵主要通过身体力行和每年3次的经营会议及每月一次的高级管理干部研讨班、每年一次管理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来传播其思想,影响人们的行为。侯为贵很少制定战略,也从不去推行一套全面适用的规章制度,而是更喜欢权变,即便侯为贵本人,也并不刻意将自己的想法加在全公司的头上。当然,这一定程度导致了中兴的执行力不如华为,但是,一旦公司面临困难时,来自基层的力量又会凝聚起来。
相反,任正非的观点在华为享有权威,高管能上能下,任正非通过自己的文章来传播思想并影响人们的行为,并把每次会议作为开展思想工作的途径。在华为,《华为基本法》就是法律,而且对公司做什么、不做什么都有规定,比如其中就规定华为永远不进入服务业和终端等,现在华为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这个限制,但《华为基本法》是不会改的。在往年新员工的培训会上,任正非都会慷慨激昂地发表讲话,其中用得最多的字眼就是“奋斗精神”、“速度”、“冲刺”、“破釜沉舟”、“活下去”、“自我批判”、“脱胎换骨”、“重新做人”等。
从总体上来说,侯为贵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企业家,只不过他是一个倾向于学习西方企业经验的东方企业家;而任正非则更接近西方企业家的特点,只不过他是一个对中国环境有深刻理解的西方企业家。所有这些基于企业家个人的不同,已经成为这两家企业最本质的差别。
3
他们那一代的企业家
侯为贵、任正非、张瑞敏等这一代人多数生于1949年前后,堪称“共和国一代”,其地位虽然未必比得上日本的“昭和一代”,但是故事性和历史价值也不遑多让。
这群人,以1940年代为轴、普遍出生于解放前后,正值国家150年深重苦难跌入4000多年的谷底,在这群人的出生簿里,饱含了洗刷掉民族伤痛的文化基因;
这群人以“老三届”为成长主轴,很多人都抱着一腔热血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,但是很快又陷入到文革中难有用武之地;
这群人,在改革开放后不像文革一代面临需要补课的局促,而是可以把当初未竟的事业心和新的机遇结合到一起、开启一场人到中年的创业;
这群人,强韧的意志,让他们在市场经济之前就能与体制斗而不破、并最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转型;
这群人,在上世纪90年代、2000年代的新生代企业家崛起之后,仍然把“奋斗”作为个人的标签善始善终,“与天奋斗,其乐无穷”。
回放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企业家的经历:童年经历苦难、少年阳光灿烂、青年压抑求索、中年奋起创业、老年伏枥而不辍……这种大历史画卷里的人生跌宕,与他们始于上世纪80年代、历经30余年创下的企业功业,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。
时势造英雄,亦或英雄造时势?其实,人终究是时代的人,时代也是人造就的时代。
这一代企业家30年背负和追索的是中国崛起的使命,正如“中兴”初始的寓意就是:中国兴旺。时代虽然变幻,中兴虽混合制而非国企,但是底色仍存。
与之相似的是,同城的华为,最初寓意也是“中华有为”;而国企管理者董明珠总是最热衷强调格力的技术……笔者最想说的是,在一个贩卖情怀的年代,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真情怀。
中兴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个缩影。而在这30年背后的整个中国,也经历了人才再造、技术再造、体制再造三重再造——中国之所以能完成这样的转型,与中国有一群这样的企业家有关:在市场经济尚未露出晨光,他们就出发了;当时的道路都是崎岖小径,前面人走的多了,后面的人也就有了路。
其实,一个企业背后都是一个故事,一个故事背后的主角都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企业家,而一个强国的背后一定需要站着一批优秀的企业家,有情怀、有脊梁,不抱怨,不浮华。
随着第一代企业家的陆续引退,未来中国还有没有以家国为情怀的一群企业家?有没有源源不断产生更多优秀企业的制度保障?还是只是有很多富豪级商人?
To be,or not to be,这是企业家的选择,也应该是时代和制度的选择。
- END -
战略升级能力是战略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。通常绝大多数公司战略最终没有成功落地,一定是战略升级的两大保障系统和十大关键步骤出了问题。
非常多的企业,很重视战略管理,但后期的落地保障、升级能力、机制建设能力没有跟上,导致战略失败,非常可惜。
SHELLBOX
為手機防護而生